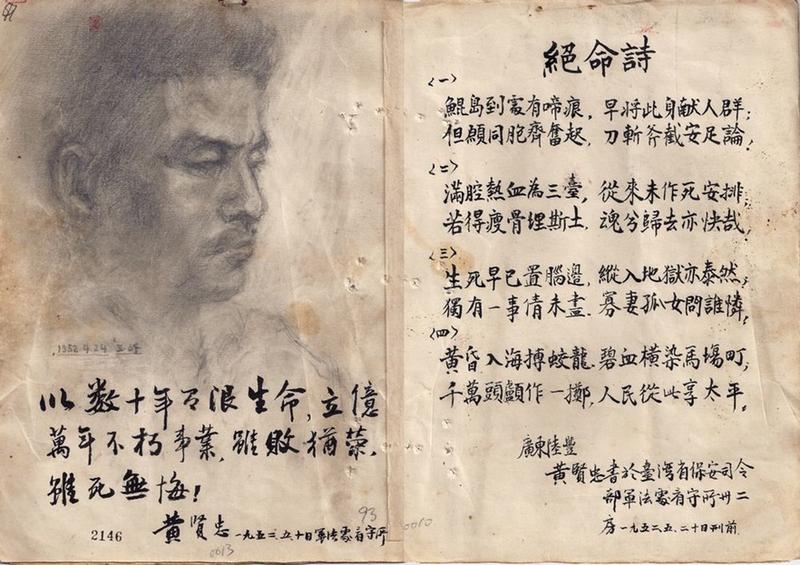評論

面對那些墜入「歷史縫隙」的人或問題時,我們該如何是好?它們有時彷彿像永無解決之路的難題,迫使人面臨苦澀抉擇。然而,我常常想著,有種來自他者的「尊敬」或類似事物,必須是在一個國家或社會選擇了挺身面對之後,才得以取回的,不是嗎。
「在台灣捲入228事件遇害的沖繩人」一案,或許正屬於這類問題的一例。
沖繩縣浦添市的青山惠昭先生今年高齡72歲,他指稱自己的父親在事件中遇害身亡,對台灣政府提出賠償訴求。這項訴訟於2月17日做出判決,台灣高等行政法院對台灣政府,做出了命令其支付600萬台幣的宣判。228事件紀念基金會決定放棄上訴,確定這項判決,就是青山先生完全勝訴了。
今年1月底,筆者為了訪問他面對宣判在即的感受,而和青山先生在浦添市見了面。青山先生對我說,「一定會輸吧。可是我會一直抗爭到最高法院的,這一仗現在才開始。」語中對這次的判決很是悲觀。
這是因為,台灣負責賠償事宜的228事件紀念基金會,在經過聽取倖存者證詞等訪問調查之後,曾一度內定許可了青山先生的賠償案(對死者賠以滿額60個基數)。然而台灣的內政部卻表示「首先,事件賠償處理條例不適用於外國人,其次,台籍日本兵與台灣慰安婦都尚未獲得戰後補償」,以此為由,介入賠償案,認為基於「平等互惠原則」不予賠償。這段賠償遭否決的經歷,是他如此悲觀的原因。 判決宣佈後約30分鐘,我透過手機與人在台灣的青山先生通了話。「結果是敗訴嗎?」面對我出於先入為主的錯問,青山先生這麼說:「是徹底勝訴。雖然很難以置信,但我贏了。家父的遺憾得雪,我想對台灣法院的英明裁決表示肯定,這場劃時代的判決跨過了負與負的連續。」他有些亢奮地道出對判決的感激之情。
1947年2月28日在台灣發生的「228事件」是場歷史性事件,它改變了戰後台灣的命運,促成了今天台灣意識的茁壯,以及民進黨與獨立勢力的崛起。另一方面,不論是在戰後的台灣或日本,卻都幾乎沒有討論過捲入這場事件而遇害的日本人,亦即來自沖繩的人,可能為數不在少數一事。
第二次大戰落幕前的50年裡,沖繩與台灣同樣都是「日本」。沖繩先一步在明治維新後的南進政策下,於1879年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並廢除琉球王國另設沖繩縣;而後台灣則在日清戰爭(甲午戰爭)結束後,於1895年割讓給日本,從此沖繩與台灣都成為了帝國日本的領土。
在經濟層面上,台灣在日本統治下獲得了比沖繩更高度的經濟發展。於是許多人從沖繩來到台灣,透過漁業、農業、家務幫傭等各式各樣的形態遠赴來台工作或是移居,在這裡展開生活,台灣和與那國島及石垣等先島群島之間,也有著緊密的海上交流。當年住在台灣的日本人中,也以沖繩人稍屬多數,堪可說是半內化似地存在台灣之中。
228事件,是肇始於對私菸販者動用暴力,隨之引發台灣民眾暴動的事件,而當年國民黨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其腐敗無能引起的廣泛民怨,則是事件的背景因素。當時台灣全島都湧起了激烈的抗議行動,但隨後自中國登陸的國民黨軍隊,卻在沒有經過正當審判與調查的情形下虐殺了許多民眾。
其中,留在台灣的沖繩人們,遽聞因為無法理解國民黨方面使用的北京話,而不名就理地遭牽連,並且遇害。尤其當時沖繩人聚落所在的基隆和平島(當年稱為社寮島),那裡被認為發生過對台灣人的劇烈肅清,因此很可能跟著整個聚落一起捲入其中。有研究者推估遇害人數達30人,但實情尚無從知曉。
這次提出訴訟的青山惠昭先生,雙親分別為來自鹿兒島縣的父親惠先先生,以及身為沖繩縣人的母親,他是夫妻倆在基隆和平島生活時生下的孩子。所以青山惠昭先生也是「灣生」,只不過他幼時便離開台灣,因此幾乎沒有任何在台灣的記憶。父親惠先先生當年隨軍遠征越南,並在那兒迎接戰爭的落幕。母親與年幼的青山先生配合國民黨的日本人遣送方針,在1946年回到日本鹿兒島,然而陰錯陽差地,對此一無所知的惠先先生卻為了接回家人,反而在遣返回日本後立刻折回了基隆,接著不幸遇上228事件爆發,從此不知所蹤。
青山先生的母親雖已亡故,但生前從未再婚,一直盼著丈夫回來的那天到來,據說煩惱得生了心病。
針對被捲入228事件的遇難者或受害者,台灣方面設有以賠償金彌補的補償制度。青山先生原已對日本行政單位提出父親的「死亡申報」,於是他先將父親的狀態改回「失蹤」,並在這道手續後,於2013年申請賠償。雖然他獲得基金會認可為受害者,但同時卻因台灣政府方面主張的「對等互惠原則」而求償遭拒,青山先生於是針對基金會向法院提起了訴訟。
這次的判決中指出,台灣政府方面主張的所謂「對等互惠原則」不適用於228受難者,並認為「規定中並無摒除外國人,應當支付賠償」。與青山先生相同,認為家族中有受難者,準備提出賠償要求的日本人另外還有3名。除此之外,和平島裡面據悉還有朝鮮人聚落存在,非台灣人但同受牽連的人,想必還在所多有。只不過228事件申請賠償的期限為2016年,剩下的時間很短,因此這次的判決應當不會致使外國人的賠償申請極速增加。
在這裡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台灣的判決奠基於一種高位視點,要求政府對外國人也應施與公平客觀的待遇,而有此決斷。對於此事,身為日本人的我們不該僅止於表達肯定,而應設身處地換個立場想想。
如同台灣政府方面主張的,日本在戰後對於據說達20萬人的台籍軍人與軍眷(其中有3萬人戰死)的補償,僅有在1990年代頒發給死傷者家屬的200萬日圓慰問金,至於未發付的薪資與恩給金的支付卻都未執行。1952年締結日華和平條約時,這個問題遭到擱置,在那之後也從未解決,就這樣到了日中兩國交往正常化,隨著日本與台灣斷交,就各種意義上愈發難有解決之道,這就是一路下來的經過。對於台灣人的補償也正如同沖繩受難者一樣,可以說是墜入了「歷史縫隙」裡的問題。
當然,我也明白對台灣人的戰後補償問題,其中有著日中關係、對台外交承認與否等複雜的面向存在,和本次228事件以個人為對象的補償問題相較,應審視的法律應對層級稍有不同。但即使如此,在戰後已逾70年的現在,對於這些依舊真切地存在於眼前的「應受補償之人」,即使已漸失先機。
台灣已給我們做出了榜樣,不論日本人也好,日本政府也好,都應該超脫國家和法律的框架,用再更多一些的真誠面對。這些事,正是經過這次判決所該我們思索的,不是嗎?
(閱讀英文版,請點:An Okinawan's Unlikely Victory Over Reparations For 228. Does It Offer Lessons For Japan?)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