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是一場白日夢⋯⋯」4月21日,40歲的林金貴從台南監獄走出來,見到了將近9年沒有看過的開闊天空。林金貴涉嫌10年前一起計程車殺人事件,但警方當年僅憑目擊證人口供循線逮捕他,如今他的辯護律師團提出新證據,透過他在案發前拍攝的大頭照,以及專家分析監視器畫面的意見,主張他不是兇嫌;法院認定足以動搖原判決,裁定准予再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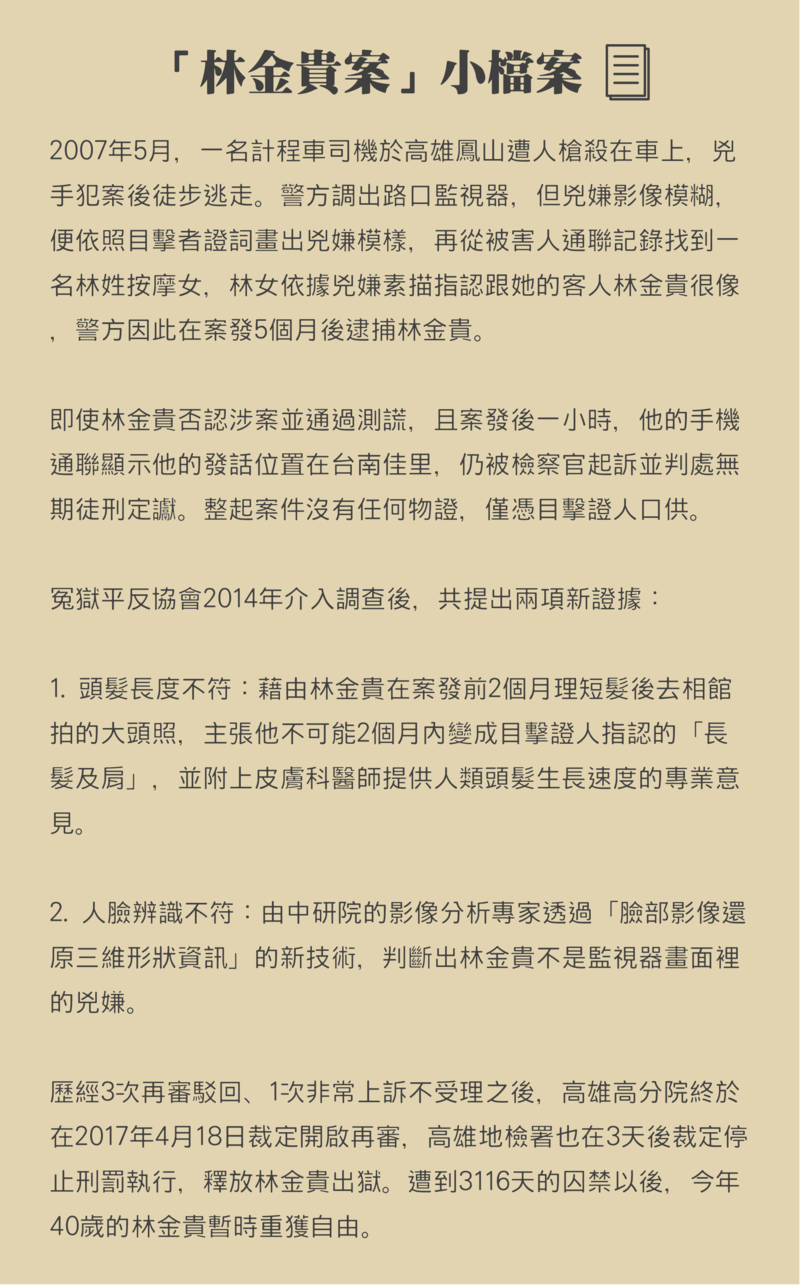
蔡晴羽是林金貴案再審聲請狀的主筆律師,與她一同調查的成員還有羅秉成律師、冤獄平反協會成員羅士翔、台大科法所學生周慶昌與蔡惟安。2014年9月,羅秉成在台大法研所開了一門「冤獄救援實錄」的課程,蔡晴羽、周慶昌和蔡惟安都是修課學生,在課堂上接觸到林金貴案,並進一步投入救援。
他們究竟如何走到聲請再審成功的呢?蔡晴羽回想當初救援小組分頭找線索時,竟忍不住大笑。她說,這次開啟再審,「林金貴的髮長」是其中一項關鍵新證據,而周慶昌特別堅持此事,不斷表示犯案兇嫌長髮及肩,但案件發生前數月,林金貴應是短髮,頭髮不可能長那麼快,「但我總覺得很瞎!」直到周慶昌和羅士翔找了皮膚科醫師出具意見書,蔡晴羽說,她才開始覺得這個證據「好像有點厲害!」
蔡晴羽的這句「我總覺得很瞎」很有意思──關於冤案救援,曾平反蘇建和案的羅秉成律師說過「要翻開每一顆小石頭」,意即對每一個小細節都要抱持懷疑,重新檢視。但實際操作時,真的可能每一顆小石頭都翻開嗎?會不會有些石頭長得根本不像石頭?對待每一顆石頭時,又該怎麼分配翻動它們的力氣?
這可透過林金貴案的每一位救援成員來探討,周慶昌說,他那一陣子就連去剪頭髮時,都問理髮師一般人的頭髮到底一個月能長幾公分?理髮師回答一公分而已,他興奮得立刻打電話給羅士翔報告。
但周慶昌解釋,他並不是特別執著在這個點上,「而是很絕望,所以心裡有任何疑問時,都會死抓著那些疑問,而且林金貴是我第一個做的案件,剛做的時候,會沒有辦法接受冤罪這個事情是很難救的,絕望感會比較明顯。」
事實上,周慶昌隱約記得,羅秉成的冤獄平反課堂上就有其他同學提出「頭髮長度不符」的疑惑。重點來了:如果把一樁樁疑似有冤的案件攤開來,許多人都可能產生「好像哪裡怪怪的」的感受,但如何將「怪怪的感受」聚焦為疑問,再把疑問問到很具體,正是冤案救援過程中最困難的地方。
就頭髮長度這個證據來講,如今旁觀者看來好像很簡單,思考上是這樣的套路:兇嫌犯案時是長髮 ▶ 林金貴當時不是長髮 ▶ 照片可證明髮長 ▶ 找出林金貴當時照片 ▶ 證明當時的林金貴不是長髮 ▶ 林金貴不是兇嫌。
但蔡晴羽說,對當事人而言,很難如此線性地推論、按部就班地佐證,「在當下要如何連結哪些經驗去證明,不是一般人自然而然能想到的事」,否則林金貴的大頭照也不會在抽屜躺了10年才派上用場。她說,有關林金貴的髮長,其實很多人問過他的姊姊,但除非很精準地詢問「妳有沒有他當時的照片」,接收問題的人不一定能意識到「他頭髮多長」代表什麼意義,以及問題可以擴展到哪裡去?
周慶昌、羅士翔在追查髮長線索時,「證明」也不是一步到位,尤其林金貴案發生時,尚不是一個Facebook盛行,人們時常打卡拍照的年代,找照片這件事並不容易。林金貴曾因竊盜罪入獄,且在計程車案發生前幾個月才出獄,照理說頭髮很短,所以他們首先問過監獄,林金貴離開時有沒有拍照?可惜一無所獲。有天羅士翔隨口一問林金貴的姊姊,她才意外從家裡找出林金貴在案發2個月前拍攝的短髮大頭照。
從後設的眼光看起來很直線的路徑,對當時走在路中間的人來說,其實相當迂迴。

話說回來,蔡晴羽最初又為什麼不覺得髮長證據很有潛力呢?與她進一步談論後發現,她一直都留長髮,對於「頭髮生長」實在沒什麼概念,在無感的狀態下,她自然不會太考究地看待這條線索。換句話說,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不同,注意力集中的對象也不同。
在好幾個人共同戰鬥的前提下,這倒是一個互補的局面,有人追查髮長的時候,有人追查其他的線索。不過,每一條線索最後是否發展為有力證據,也不一定是努力就可以決定的事情。
另一位救援成員蔡惟安最初接觸林金貴案時,想主打的重點是鑑識現場、彈道比對等等,希望將整個案發過程都更清晰地重建,說不定會有新的發現,「但後來沒有繼續下去,可能也因為我自己沒有多堅持,而且很多資料在警方手上,我們只看到很簡略的報告,取不夠多素材,也沒辦法再去請專家或找更多專業協助。」
這一切聽起來相當微妙,有些冤案之所以成形,是因為客觀條件與主觀意識的侷限,救援冤案就是要破除這些侷限,但不管再認真,難免也受到客觀條件與主觀意識的侷限。
蔡晴羽分享了另一件案子給她的心得。一起車禍肇事逃逸案件中,警方憑著目擊證人記下的車牌找到被告,但被告喊冤說肇事者根本不是她。再審開庭時,檢察官不斷詢問報案紀錄,要法官再查一次,對於檢察官重複要求函查已經函查過的資料,蔡晴羽很不耐煩,但法官再查一次之後發現,報案紀錄裡寫的是另外一台車,這個發現對被告是有利的。
這個意外的轉折讓她非常驚嚇,那是一種「到底應該要懷疑到什麼程度」的衝擊感,她也很驚訝,原先可能對被告不利的事情,其實竟然是有利的。但若她當時成功阻止法官再查一次怎麼辦?會不會很久很久以後,都還不知道是誰在哪個時間點做了哪一個動作,妨礙了真相的出土?
這件事讓她想起2012年最高法院作出一項原則性的決議──法官不可以再主動調查不利於被告的證據。當時法律界掀起一波論戰,許多人認為還沒調查之前,怎麼知道某條證據對被告有利還是不利?「那時候我心裡覺得這是屁。心裡想說,最好是啦!還沒調查之前通常也知道對被告有利還是不利。但冤案救援過程中很多事情是顛覆你的想像和常理的。」
蔡晴羽從台大法律系畢業後,很快就到一般的事務所當起執業律師,近年才投入冤獄平反協會,「我以前不會想那麼多,因為律師就跟法官、檢察官一樣,手上有很多案子,案子一直在前進,每件案子就是一直在前進,所以你不太會去反省過去的自己。不能怪法官、檢察官,連律師都不會啊,誰會沒事說定讞的案子我還要去看看卷、哪裡有疏漏?」
「所以冤案救援就是,你會變成逼自己要從另外一個視角,回去看自己過去做的每一個決定、每一個辯護策略,因為你等於是從事後的觀點去回推。那個反省的力道還蠻驚人的,跟我們平常做事情還蠻不一樣,平常就是什麼都在往前看,看手上有什麼,要面對接下來的開庭,面對接下來的證人,可是做冤案救援,什麼事情都在往回推,很多東西都要去質疑到底做得怎麼樣。」
救援團隊裡最資深,也擁有最多冤案救援經驗的羅秉成律師,又是怎麼看待髮長證據的呢?他說,他相信這可能是一個證據,否則不會繼續追查,但還是覺得髮長證據相對薄弱,因為人們很容易就可以丟出一個說法,說兇嫌犯案時戴假髮,「是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但這樣講不公平也不合理──排除責任在誰身上?如果案發後馬上逮捕他,去他家搜出一頂假髮,或許還可以連結說他可能戴假髮,或者,你要證明他平常有戴假髮的習性。」
即使這種有罪推定的質疑不公平也不合理,光是有人會產生這種疑慮,就可能讓這個證據弱掉,羅秉成說,他必須想像如果自己是法官,看見怎麼樣的證據才很難駁回?因此,他等到「人臉辨識」那條線索也有結果之後才出手,得到加乘的效果。
也就是說,救援冤案的時候,羅秉成真心考慮一切的可能,但用最壞的想像去做準備。不過,他也對「考慮一切的可能」這件事頗有感觸。
「救援確定案件而不是發展中案件的優勢是,我們看到全部的東西,但全部的東西也在限制著我們。關於發展一個新的議題、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什麼應該走下去,什麼應該停止,幾乎是沒有答案的。有些走到底,浪費許多時間,是死胡同⋯⋯有些需要一點運氣、多一點材料才會往下延伸。有些時候你沒有去碰撞,去try,後面那條路就打不開,但有時候後面那條路打開的力量也不在你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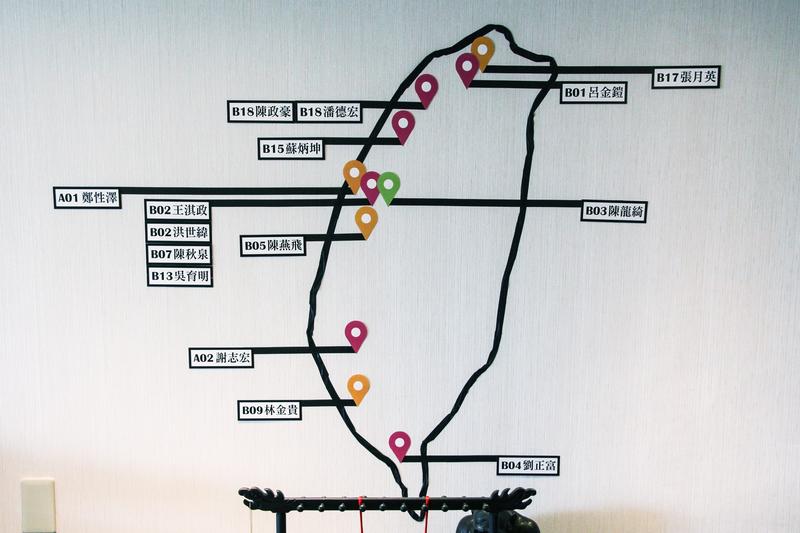
無論是羅秉成、蔡晴羽、羅士翔、周慶昌或蔡惟安,每一個人談起林金貴案及其他案件的救援歷程時,都謙卑地提到「運氣」這個因素,並滿懷感謝。那是因為他們在冤案救援的途中,真正深刻地體察到有太多不可抗力,且每一個人都不是「全知全能」,都可能犯錯或疏忽,但作為任何一個環節的司法工作者,微小的錯誤或疏忽將影響他人命運時,就必須不斷地、嚴苛地自我修正。
透過修正而累積起來的里程數,他們抵達一個更接近公平的地方。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