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通過亞洲第一部保障病人醫療自主權的《病人自主權利法》,民眾在二親等家人陪同下,與醫療人員進行自費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簽署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 AD),決定特定臨床條件下的善終方式。
但專法2018年公告、試辦3年,實施將近2年,每千名符合資格的國人僅3人簽署,形同99%的人未受益。今年受疫情影響,民眾非必要不去醫院,AD簽署人數下滑。此外,專業諮商團隊衍生高人力成本,2,000元起跳的諮商費成為民眾踏入診間的最大障礙,以「團體諮商」減免諮商費等鼓勵措施應運而生,AD諮詢的質和量之間如何權衡?為何《病主法》成為從事末期照護醫師口中「『好到難以執行』的法案」?
週一下午,嘉義陽明醫院會議室排排坐著幾名頭髮斑白的民眾與陪同家屬,前方螢幕投影預立醫療決定表格,院長謝景祥逐一解釋當民眾遇到疾病末期、不可逆轉昏迷、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其他痛苦難以承受疾病等臨床狀況時的「特殊醫療拒絕權」。
「醫師,如果我以後失智了,要人家餵食和清理大小便,是不是就可以執行這個(預立)醫療決定?我不想活得沒尊嚴!」坐在第一排的廖阿姨發問。
「不見得,這會交給兩位相關的專科醫師確診,他們會用量表幫妳看,要符合才可以,」謝景祥說明,符合AD啟動條件的病人時常已呈現類似昏迷狀態,恐怕吞嚥都有困難。
「到插(鼻胃)管的程度才可以啦,要選擇妳想不想用鼻胃管!」一旁的楊伯伯補充。
廖阿姨起頭後,各種問題跟著冒出來。
「我簽過DNR(Do not Resuscitate,拒絕心肺復甦術),跟這個AD有什麼不一樣?」
「所有管子都不插,可以撐多久?」

有如課堂討論的場景,在現行的ACP並不常見。雖不乏醫院為推廣AD簽署,推出2到3人同行的團體諮商優惠方案,但適用條件多為二親等內親屬或至交好友。陽明醫院在2019年、2020年兩度推出團體諮商,不過同場者多半素昧平生,相較一對一的諮商,更像一對多的講解。
另外,在以家族為單位的諮商當中,家人情感的梳理最費時,生死大事當前,從前說不出口的情緒與牽掛都要談開,釐清彼此心中的生命意義再做善終選擇。有的諮商不僅AD表格,連後事安排都一起談。而在《報導者》取得嘉義陽明醫院ACP意願人同意旁聽的這個場次,大家的疑問以法條本身與執行面為主,較少涉及家族事務。
意願人一面聽謝景祥解答、一面討論,問題告一段落,謝景祥與一名護理師、一名心理師、一名社工師協助意願人簽署AD,為他們解答其餘不清楚的問題,最後完成簽署,過程約1小時。
ACP結束,廖阿姨有感而發:「我(簽署AD)意願是非常高的,但要是像其他醫院得收3,000塊,我根本不會來。」
國際領隊退休的59歲廖阿姨跑遍世界各地,對生死事很看得開。她很早就認定自己要死得有尊嚴,傅達仁赴瑞士醫助自殺的新聞讓她尤其關注,「台灣沒有安樂死,我無法像傅達仁那樣花300萬去瑞士,但就是不想萬一變植物人時還拖磨,讓經濟拖泥帶水,連累醫療體系,女兒徒增煩惱。」
她明白諮商團隊辛苦,但就是不懂為何要花錢選擇自己怎麼死。她日前到嘉義陽明醫院看診時得知免費ACP消息,立刻報名。
61歲吳阿姨參加銀髮族瑜珈班,老師在陽明醫院完成免費ACP後,將《病主法》概念帶到班上向學生推廣。聽到能安排自己的善終,還是免費,同學報名熱烈,分好幾梯才完成諮商。
2019年起,嘉義陽明醫院推出限量的免費團體ACP,醫界看法兩極,卻在民眾口耳相傳下反應熱烈,讓這間小型地區醫院在2019年累積1,011份AD簽署量,僅次台北市聯醫、台北榮民總醫院兩大體系。
骨科醫師出身的謝景祥,家人曾在癌末受到許多不必要的痛苦。創立嘉義陽明醫院後,他響應健保政策設置呼吸照護病房(RCW),又因此見證無數「當生命只剩呼吸」的掙扎。他很認同《病主法》理念,希望盡速將民眾納入保障,減少種種難以壽終正寢的悲劇。
相較繁忙的大醫院,謝景祥認為醫病關係更熟悉緊密的地區醫院和診所更適合推動ACP,他申請讓陽明醫院成為可執行ACP的醫療院所,「馬上發現收錢諮商一定做不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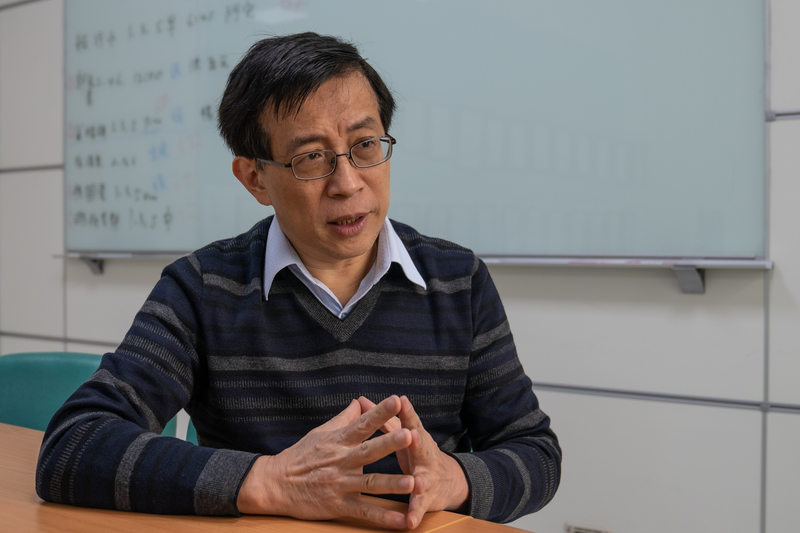
錢與人,是《病主法》中兩道環環相扣,讓專法難以落實的障礙。一次ACP得出動受過訓練的醫師、護理師、社工師或心理師,每次平均60到90分鐘,人力成本高昂,衛福部規定一次諮商費為2,000元到3,500元。不過諮商門診是未雨綢繆性質,不在《全民健康保險法》規範的「疾病、傷害、生育事故」給付對象內,民眾得自費。
「這讓ACP成為《病主法》成功的基石與絆腳石,」謝景祥認為,諮商自費、程序複雜、諮商機構太少,都削弱民眾走進ACP診間的意願。
謝景祥曾建議總統蔡英文和衛福部提撥5年50億公務預算,補助250萬名65歲以上民眾做ACP連帶觀念推廣。他的概念是,每年健保總額7,000多億元,近3成是用在生命最後3到5個月。預立醫療決定能降低臨終無效醫療的成本,也是為健保省錢,當大部分的人都了解《病主法》,就可簡化諮商程序降低費用或取消諮商,但未獲正面回應。
為證明諮商費是推動《病主法》的關鍵因素,謝景祥決定讓陽明醫院當「對照組」。他2019年運用衛福部50萬元獎勵計畫,再自掏腰包補足經費,推出600個免費諮商名額。但考量人力成本,諮商並非一對一進行,而是採一個諮商團隊對多名意願人的諮商方式。
民眾預約後,個管師會先致電講解流程,這群多半素不相識的意願人,再於固定時段到醫院一起聽ACP團隊說明簽定內容與要件,有問題當場提問,想再細問可到辦公室私下晤談,最後完成簽署。
600個名額迅速額滿,每場次平均20多人,有苗栗寺廟的師父專程包車南下,謝景祥也曾帶ACP團隊到扶輪社例會做諮商。因預約踴躍,他加碼免費名額,4個月共完成769例。
今年5月底開始,謝景祥再度運用衛福部的ACP獎勵計畫經費開辦限時的免費諮商,依今年獎勵計畫的新規範,每場ACP頂多5名意願人,口耳相傳下幾乎場場額滿。

與陌生人共同進行的講座式ACP,能迅速累積AD簽署量,卻在醫界引起不少質疑。
「本來應該是精品店,卻變成量販店,」馬偕醫院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主任方俊凱直言,這樣的諮商沒有違法,回到《病主法》的立法精神,卻有些「怪怪的」。「品質夠好嗎?能有細緻、深入的溝通?ACP量多,不代表品質好,希望大家是真的懂了才簽。」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祕書長、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彭仁奎也持反對意見,「演講場合可以做衛教、推廣《病主法》觀念,要產生法律文件(AD)恐怕不適合。如果沒有深思熟慮、也沒有經過跟家人溝通的過程,前端簽得輕鬆,但後端預立醫療決定啟動時,會有很多問題,造成醫療現場的諸多困境。」
台灣「安寧之母」趙可式則認為有好有壞。好處是諮商過程集體討論,或許別人問出自己想不到的問題,或原本不認同《病主法》的家屬,經過大家意見交流後產生不同想法;壞處是有些隱私問題實在問不出口,一對一較能暢所欲言。
「當然一對一品質好,但每個人對品質的要求不同,」謝景祥說,他遇過早就和家人談妥,只盼到院花5分鐘完成AD簽署程序的民眾;也有和單一家庭諮商1個半小時,家人間仍無法達成共識的案例。嘉義陽明醫院的簽署者年齡集中在5、60歲,很多都是剛送走父母,歷經長輩往生前各種為難的抉擇。這群人對自己的臨終決定有想法,免費是多一個誘因,促使他們起而行。
他也強調,團體諮商不代表照單全收,意願人和家人嚴重意見分歧,或意願人有失智等情形,團隊評估後沒把握對方能真正理解AD內容,都不會讓他們簽署。
這樣的ACP模式少了與家人的互動商討,不過嘉義陽明醫院的ACP團隊認為,換個角度想,這也給意願人了解其他家庭價值觀的機會。
團隊的心理師陳穎彥、社工師張雅筑表示,有些意願人來諮商前已經很確定AD要怎麼勾,聽完別人意見,或許會有更廣的思考方向。簽署時,諮商團隊會個別詢問每位意願人狀況,協助他們在聽過眾多想法後做出自己的決定,如果無法馬上下筆,可以下次再來。
對廖阿姨與吳阿姨而言,她們倒沒深究何謂ACP的「品質」,只想透過這個流程完成她們的善終心願。
「瑜珈課老師有和大家討論,我每個選項都想好了,今天來『上課』聽聽別人的看法也不錯,」吳阿姨說,家人早就知道她要來簽AD,沒辦法陪同諮商,但都很支持。
同樣沒有親屬陪同的廖阿姨,也早就打定主意每個選項要怎麼選,「我回去會把AD副本拿給他們,告訴他們這是我的意願。」

現象1:不只家人,好友、師生也會一起來諮商
既然諮商成本不可避免,衛福部在2019年1月《病主法》初上路時,就鼓勵醫療院所規劃「同一時段第2人次可減免諮商費」,促使意願人家屬一起諮商。根據衛福部網站,目前全台199家提供ACP諮商門診的醫療院所,有7成提供團體諮商方案,執行方式與優惠各有不同,有的從費用上減免,例如同行第2人起諮商費500元、同行第4人以上免費;或以便利性出發,開放企業預約團體諮商。
ACP免費是一大誘因,減免諮商費就不見得。2019年AD簽署2,273份,數量最高的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體系,民眾仍採個人諮商居多,以團體諮商模式完成簽署者僅13.15%。
部分團體諮商有其必要性,病人自主研究中心、罕見疾病基金會、台灣弱勢病患權益促進會今年與台北市聯醫等醫療院所合作,主動為有較高生命風險的罕病患者做ACP,除了罕病患者,還補助其兩位家人共同諮商,希望可以發展出服務模式,為弱勢族群採取更積極的保護措施。畢竟患者與照顧者是「生命共同體」,一人倒下全家崩潰,都需趁早做出善終決定。
「理論上,若是同個家庭多人一起諮商,我覺得不錯。一來諮商費有優惠,再者家人能藉機溝通交流。非血親也能一起做,前提是對彼此非常熟悉。」
《病主法》立法推手、病人自主研究中心執行長楊玉欣發現,隨家庭結構樣貌日趨多元,團體諮商的「組合」也從親屬、伴侶拓展到朋友,例如有的高齡長輩與孩子沒那麼親,反而想和同齡好友住在一起養老。「這尤其可能出現在經濟狀態好的族群,他們覺得孩子久居國外有距離感,準備共度餘生的朋友才是一起諮商、擔任彼此醫療委任代理人的對象。」
台中榮總緩和療護病房醫師黃曉峰則遇過外籍老師與兩名學生一起來諮商,3人都沒結婚,相識多年感情很好,已算是意義上的家人。3位師生的二親等都沒來,他們互為彼此的AD簽署見證人。「團體諮商不見得要家人,能相互支持、很了解彼此就可以了。」
雖然《病主法》規定二親等內親屬至少一人須陪同諮商,實際執行時卻發現,包括榮民、街友、家庭疏離者、子女久居國外等原因,都很難找到符合規定的陪同者。因此只要意願人提出書面切結仍可做ACP。不過黃曉峰與楊玉欣都認為,除非有特殊理由,仍會請意願人盡量帶家人參與,畢竟若家屬的觀念和意願人不一致,醫院執行AD時會非常為難。「《病主法》將諮商入法,也希望用法的剛性帶動家庭溝通,」楊玉欣說。
現象2:同場次、多位意願人

ACP的最初設計為個人諮商,根據試辦期間經驗,平均每人次ACP就需耗時60到90分鐘。當同場次的意願人一多,諮商資源被打散,能維持品質與細膩度,並讓意願人自主表達嗎?
台北市聯醫2019年開辦以家庭為單位的團體諮商,2020年則啟動「企業團體諮商」,讓ACP團隊前往有意將《病主法》推廣給員工的民間企業或NGO,每場最多3個員工家庭、共9個人。 台北市聯醫社會工作室主任楊君宜表示,1個團隊對9個人,很多AD上的選項會變成只是勾完,所以除了醫、護,還會視人數出動2名以上社工師,第一階段的法規說明大家一起聽,之後以家庭為單位分組各自帶開諮商,以免相互干擾。
「出發點當然是希望愈多人知道愈好,員工原本就對《病主法》有一定認知,再說二親等都陪著來了,為什麼不也探討自己的善終?」方俊凱說,希望累積團體諮商經驗後推廣給民眾。
但他發現,團體諮商時,意願人的選擇不免受同儕影響。有人看到家人在諮商後決定不簽,自己也開始搖擺不定,個別諮商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楊玉欣表示,和別人的決定不同一定有壓力,這時專業第三方的諮商團隊要幫忙撐腰,在諮商過程觀察這個家庭的權力關係如何,幫助相對弱勢者做自主決定,幫助相對強勢者學習尊重家人。而在團體情境中,不免有人很會發問,有的較不發問,會發問的人會有領導作用。識別較沉默者是真的沒想法,或是有想法不敢說、不知道怎麼說,考驗諮商團隊的實力。
她建議,團體諮商的意願人可一起諮商、發問,但除非是互為見證或醫療委任代理人,簽署AD的決定階段其實可以分開做,降低意願人彼此干擾。

楊玉欣認為,無論個人或團體ACP,諮商品質好壞都與諮商團隊能力息息相關,但現行的教育訓練不足,也沒機制把關諮商品質。
《病主法》規定,醫師受4小時訓練,護理人員6小時,社工人員與心理師11小時,即可提供ACP諮商,這看在楊玉欣眼中遠遠不足,更何況團隊中溝通能力最弱的醫師,訓練時數卻最少。「《病主法》很複雜,我很懷疑能用6個小時了解法規,還要會諮商。」
病主中心曾與台北市聯醫舉辦每場21小時的《病主法》核心講師課程,有人認為訓練還不夠,卻也不乏反映上課時數不必那麼多,真正學習是從做中學。
既然無法期待每個人都花時間投入得到深刻感動,楊玉欣認為仍得找到一套讓醫事人員病主觀念更普及的方法。病主中心2020年推出《病主法》線上課程,通過便可取得ACP人員完訓資格或累積訓練時數,同時幫助較難參與教育訓練的偏鄉醫護。
單向的線上課程,足以了解《病主法》並提供高品質ACP嗎?楊玉欣坦言,雖然線上課程涵蓋法規知能與諮商實務,但ACP的難處是如何幫家庭在意見不合、或相對弱勢者無法發聲時做有效溝通,實現當事人的自主權主張,這方面透過實體演練一定更深刻;不過若要「做中學」,至少得先取得諮商資格,感興趣的人未來再上課累積知能。
「目前整體看來,神經內外科醫師似乎不是很有興趣深入了解《病主法》,這恐怕是將來AD啟動時比較辛苦的地方,」彰化基督教醫院安寧緩和療護科主任蔡佩渝說。
彰化基督教醫院神經內科醫師、台灣神經學學會會員陳彥宇持「做中學」看法:「啟動的需求或案例較多時,神經科醫師參與得就多,藉由參與實際執行,會逐漸增加經驗與了解程度。」
想維持醫、護、社工師或心理師的ACP陣容,勢必面對降不下來的成本。減免諮商費不是長久之計,調整ACP團隊的組合,成為下調諮商費最直接的手段。
「立法者誠意太高,要把善終這件事和民眾好好地談,但是請醫師出來談,就是很貴啊!」黃曉峰嘆道:「這套制度設計得太好,好到難以執行。」
若團隊不含醫師,就能立刻壓下諮商成本。黃曉峰支持這個調整方向。「你說要有醫師作為專業人員,但跟意願人談的醫師,卻幾乎不可能是他幾十年後生病時碰到的那個醫師。」
在神經學醫師投入有限下,意願人提出的問題,恐對不上醫師的專業領域。「比如帕金森氏症老先生來ACP,請神經內科跟他談比較合理,但現在有多少神內醫生在諮商?由安寧講解帕金森氏症有什麼意思?」若只是要講法規和衛教,由公衛人員與護理師進行即可。
衛福部次長石崇良認為,想解決ACP塞車與費用問題,就要改變ACP的執行方式。他比喻,若《病主法》的施行是條高速公路,ACP這個收費站就是造成塞車的原因,因為不只得人工收費,收費員還非得是人力有限的醫護社心。如果今天拆掉收費站,在旁邊設休息站,當民眾知道要往哪去就直行,不清楚就到休息站裡的資訊中心詢問,車流會比較順暢。
他期待讓ACP成為選項而非必要條件,了解《病主法》的民眾,就像現在簽署DNR一樣直接簽AD,不需費用也不必排隊。若需專業諮商,就要收費。
拆除收費站前提是更多社會教育,民眾觀念普及前,現階段可採雙軌制,讓受訓取得ACP資格的民間組織提供諮商,降低收費,增加資源可近性。同時維持收費ACP門診,提供給希望由醫護社心諮商的民眾。
但在楊君宜心裡,ACP是《病主法》不可省略的價值核心。她日前談了一個罕病重症ACP,患者已戴呼吸器一段時間,直到做ACP,才在諮商團隊帶動下與妻子討論後事安排。家人間種種說不出口的議題,常得由諮商團隊拋出來直球對決,釐清彼此想法,才能讓AD啟動無礙。
楊玉欣也持保留態度。她認為《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立法20年、73萬人簽署DNR,臨床還是會因為家人不知情、不認同發生醫療糾紛,受苦的仍是病人本身。「ACP成為選項的前提,是要很認真地推《病主法》,推10幾20年才有可能。」

2020年上半年受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民眾非必要不去醫院,AD簽署量3,000份,是2019年簽署份數的四分之一,下半年才有回溫之勢。但回到《病主法》立法目的,「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其善終權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能被量化計算嗎?
蔡佩渝不這麼認為。她表示,ACP是幫助民眾思考、溝通,要不要簽AD是另一回事。無論民眾諮商後需要時間再想想、跟家人討論,甚至思考後決定不簽,都是「自主」,應該尊重。「把完成多少例ACP、簽了多少AD當成推動《病主法》的指標,我覺得不對。」
台北市聯醫統計發現,疫情期間取消ACP的老年病患、重症或特殊疾病患者比例很低,他們有5成抱持「不想成為他人負擔」想法,而且比例較以往大幅提升;而在疫情爆發前,最普遍的諮商動機是「讓人生最後時刻走得有尊嚴」。楊君宜認為,國外無數突然因COVID-19來到生命末期,家屬糾結是否插管急救的報導,可能也是這群人做ACP的推力。
台北市聯醫總院長黃勝堅認為,疫情固然影響ACP的「量」,但若促使民眾提早思索生死大事,就可能拉高諮商的「質」,現在正是和家人好好聊聊彼此生死價值觀的契機。
畢竟ACP與AD,都是保障病人自主落實的手段,啟動對生命的討論,才是《病主法》的真正核心。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