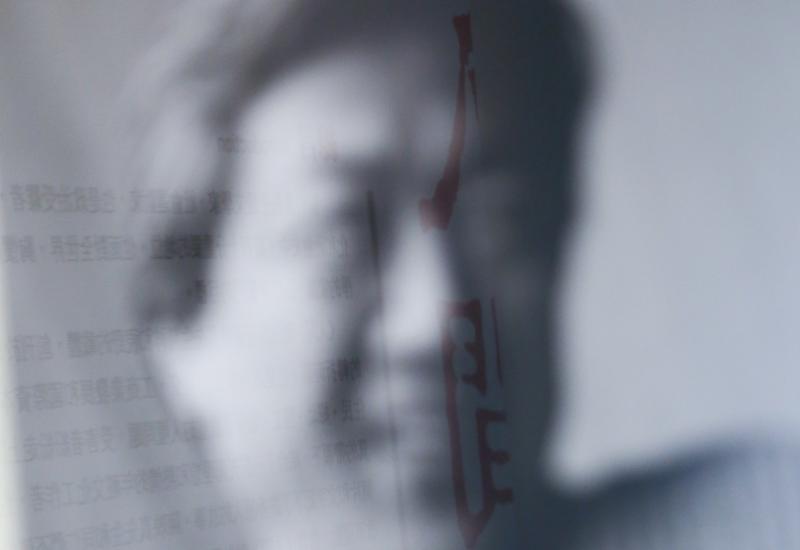近來在北美館的展覽《微光闇影》以攝影為題,聚集許多台灣攝影家。不管是當代年輕作者、又或者中青世代的作者們,都以「攝影」為基礎聚集在一起。館內策展人余思穎試圖佈置「時間性」、「歷史性」、「物理性」、「攝者與被攝者關係」與「歷史性的暗影」等5個命題,來討論這些創作者作品。
但,如果說北美館主要以作品的外在形式規劃命題與展呈,那本文將試圖以另一種不同的內在脈絡,重新思考《微光闇影》的可能性。
在彙集了大量攝影創作者的《微光闇影》展覽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世代的差異。中青世代攝影家更偏向用傳統的紀實或街拍方式看待攝影,而年輕一輩的創作者則是用更加豐富的方式展示攝影語言。而本文首先將以展覽中的紀實基礎出發,接著再考慮文化的表演與年輕作者更私密的轉向。
我們先來回顧近來在北美館舉辦過跟攝影相關的展覽。從台北雙年展《當下檔案:未來系譜》 《當下檔案:未來系譜》中有許多以攝影為基礎的作品,不過跟《微光闇影》更傾向紀實、人物或歷史的作品比起來,雙年展中的攝影作品大都以冷調的景觀記錄為主。
《舞弄珍藏》中的《對照記》跟《寫真筆談》也算是對台灣攝影創作的回顧。
王信可以說是在1980年代,投入台灣報導攝影的先驅之一。
此外,我們還可以跟去年在國美館舉辦的攝影大展《銀鹽世代》做比較。《微光闇影》就像《銀鹽世代》的升級,但卻未到當代攝影語言的活力想像(儘管這兩個展覽都選了一些年輕作者)。也就是說,《微光闇影》與《銀鹽世代》同樣遠離今天數位時代對攝影的重估,回頭強調傳統攝影底片的物質性以及關注攝影的本質。 (註)《微光闇影》有點像是攝影的傳統語言連結到當代語言的橋樑。
不過,這兩檔展覽還是有所差異,《銀鹽世代》更偏重古典技法與底片形式的懷舊情懷,抽空的談底片或技法顯影的藝術價值。而《微光闇影》卻是更加有力地連結攝影與歷史、記憶與個人的關係,也就是更加「連結在地脈絡」與「回應轉型正義的當下」。
然而,在今天的數位時代,我們對於攝影的思考或許不能僅止於攝影本格(堅持底片或見證式的紀實攝影)。在今天我們更傾向考慮「攝影是如何對我們產生效果」、「攝影作為一種異質檔案」、「用謊言來讓我們感知現實」(質疑攝影再現的本質)、「更加擴張的考慮攝影本身」。但《微光闇影》還是有不少攝影家聚焦於底片、傳統、黑白、見證、過去歷史、決定性瞬間等等,殊為可惜。 (註)可能是因為時代侷限,還有對攝影的本格信念,所以前輩對攝影的想像比較沒那麼多元。但對我來說策展人或許可以試著在展呈上活化那些攝影的僵化概念。
傳統攝影的回望
將上面展覽做對照,我們可以發現《微光闇影》的影像表現更傾向傳統的《王信攝影展》或《銀鹽世代》。此外《微光闇影》也承載了台灣政治的動盪紀錄與他者的關注。至於對檔案的再啟動,以及以今日眼光賦予傳統文件新生命的作品,則相對較少。 (註)當然,策展人將這些作品佈置在一起也是一種再詮釋。不過,在作品上,除了侯怡亭較為傾向異質檔案的啟動,其他很多都只是老照片的再展示。
13
《 微光闇影》中,劉振祥策劃的《歷史性暗影》展場。(攝影/余志偉)當我們進入展場,還是會發現《微光闇影》仍有不少偏向攝影傳統的「歷史見證」或「個人美學表現」。比方說,沈昭良的經典紀實《玉蘭》、潘小俠喝茫在艋舺的晦暗街拍《艋舺—夜巡》、林柏樑在過去偶然拍攝到的人物肖像但在今天卻越看越有味道的《私人備忘》、金成財的《寂靜的槍聲》記錄了當時不能發表的布農族狩獵文化、劉振祥策劃的《歷史性暗影》則是呈現過去受意識形態控制,難以在主流媒體發表的街頭抗爭影像。
上述作品大多落在紀實攝影的傳統範疇,尤其是「決定性瞬間」的執念。 (註)或許跟這些攝影家當過「記者」背景有關。不過金成財的作品更為私人的參與自己的文化,更讓人動容。
張乾琦還是以紀實為基礎,進而擴張紀實傳統,而非直接遠離紀實(像是展覽不在紀實脈絡的其他作者)。我知道不少人是為了張乾琦的作品來看《微光闇影》,老實說當我踏進張乾琦的展間時,也有種跟前面作品完全不同的感受。
紀實攝影的拓展:張乾琦
在《微光闇影》的張乾琦展區,除了他在龍發堂拍攝精神患者《鍊》的巨型肖像外。他也呈現錄像剪輯《Side Chain》,以及他在坦尚尼亞關注當地問題(愛滋病與毒品濫用)的錄像《Bongo》。在此,攝影不再是一張或系列照片,而是透過多媒體(照片、實地錄音、訪談等等)交織而成的影片(當然我們知道他很早就有這方面的轉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Side Chain》中,張乾琦不再只是像是傳統紀錄片的如實紀錄,而是投注更多個人視角的詮釋。比方說,他透過旁白聲音錄像作品在展覽上有附上翻譯,看起來像是患者的書信,他們對龍發堂的態度大都是某種抵抗姿態。比如,「我不想再被鍊起來了」、「我受夠了吃滿佈著蒼蠅的餿水」、「已經30年沒叫過我的名字了」等等。這些內容其實是賴如秀採訪龍發堂後,以第一人稱模仿病患心境的短文。
張乾琦臉書對於北美館《 微光闇影》展覽《鍊》的推播短片。
不過,最讓人感觸的還是巨幅照片《鍊》給人的效應。相較於何經泰《工殤顯影》對受傷勞工肖像的「直接表現」;《鍊》的鏡頭則如同鬼魅般冷冽地記錄這些龍發堂病患,這種文件般的紀錄更加讓人感受到某種隱晦又耐人尋味的不安。
如果說,何經泰是用他的熱血跟生命關心這些隱匿台灣社會的他者,更加「前進又煽動的」接近被攝者,在影像上呈現戲劇般的表現張力;張乾琦則是用冷調紀錄方式,將這些黑暗邊緣的他者如實拍攝下來,並更加「後退又不帶情感的」呈顯我們跟他者的「不可能距離」(如同「攝影再現」跟「真實」的不可能距離)。
美學遮蔽現實?
在《微光闇影》中,《鍊》的照片以大幅、環狀的方式佈置在美術館場域。然而,郭力昕曾指出在美術館裡的紀實作品遭到藝術論述的「意義暴力」──作品抹除被攝者的個體差異,造成對現實的剝削,並與藝術權力的文字迷障共謀。 (註)郭力昕以Richard Bolton批判Richard Avedon的作品為例。試圖將張乾琦跟Avedon只注重表現形式,脫離現實脈絡的問題拉在一起談。但,我認為Avedon是在讚頌那些他者的表面,確實有獵奇的傾向;而張乾琦卻不止於此,他更像是用一種不帶獵奇角度、冷靜的觀看,將這些他者的肉身顯現在場。換句話說,Avedon較偏向美學形式上的張力表現(讚頌這些古怪的美!),但張乾琦卻是讓我們反思「我們跟他者之間的關係」。
郭力昕犀利地批判:「紀實攝影礙於見證式的傳統攝影義理,通常取得了現實的表相,但難以進入現實的內核,讓人得到對脈絡性的意義理解。然而,如果藝術手法是新紀實攝影的表現概念,則新紀實攝影在藝術話語上的生產,必須一定程度地連結著特定的現實,成為表述意義的根據或線索。若仍只取現實題材的表相,然後以藝術語彙/技巧,將這些作為現實表相的影像符號,轉化為視覺藝術本身,將極可能出現對現實本身的剝削。」 (註)郭力昕(2015)。〈意義迷陣裡的權力與暴力:作為當代藝術的新紀實攝影話語──以《鍊》與《野想》為例〉。《傳播、文化與政治》,1:41-73。
要言之,郭力昕認為當傳統見證式攝影轉向新紀實攝影的藝術表現時,我們還是不能忽視「現實脈絡」,不能讓個人美學或藝術場域的權力論述,遮蔽現實的特殊性。然而,或許我們可以換個角度思考,張乾琦的《鍊》不只停留在美學/現實二元對立的範疇裡,他同時打開了某種新的可能性。他給予了新的感知模式,當大家都在近距離拍攝報導攝影與專題圖片時 著名戰地記者卡帕(Robert Capa)名言「拍得不夠好,代表你靠得不夠近。」
張乾琦這種去情緒、嚴肅的、近乎非人般不帶情感的關注,反而「政治地」挪移了我們既有的感性框架,打開了某種新可能(而不只是回到報導攝影的美學或人道關懷的窠臼裡)。我們不能只是用化約的美學形式欣賞這些照片,而是感受到某種詭異的矛盾與張力。換言之,我們不能只停留在美學/現實的二元思維(把現實脈絡看得比美學看重要,或者把美學看得比現實重要),而是轉移考慮二元對立的瓦解,與某種新感知的啟動。
一直以來,紀實攝影都帶有個人美學遮蔽現實的「原罪」。
然而,當代的義大利政治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卻提出不同看法,他說:「攝影對我們提出的急切需要與美(或者說一切美學的東西)無關,它是一種救贖的要求。照片永遠比影像包含更多:它是可感物與可理解物之間,記憶與希望之間,保有缺口與巨大的裂隙的所在。」 (註)引自
〈阿岡本論攝影:審判日〉。 這邊要注意的是,阿岡本不是回頭讚揚個人美學,他也對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或薩爾加多(Sebastião Salgado)講究美學形式的攝影表現存疑。
換言之,阿岡本把攝影傳統的美學問題,轉移到救贖的身體存在問題。《鍊》恰恰是開顯那道縫隙,召喚他者的「身體姿態」,讓觀者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照片的肉身」觀看──不是我們將他們當作美學物件欣賞,而是我們「被」他們觀看。 郭力昕在批判張乾琦的《鍊》時同時批判周慶輝的《黃羊川計畫》,但我覺得張的異質感跟身體召喚走的比周更遠,而周比較有郭所批判的問題。
紀實語言的創造性
要言之,《鍊》不只停留在精神患者的「再現」框架,而是讓展示的影像本身成為「本體」,不斷撕裂觀者的期待與人道情懷,進而不斷朝向那個外在於我們的世界敞開。用哲學家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話說:「肖像不再是去再現一個置於世界前的主體,毋寧說這是去展現一個向著其專有的視覺、向著其專有的明證性湧現的世界。」 (註)《肖像畫的凝視》 頁76 , 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著; 簡燕寬 譯;桂林:灕江出版,2015。
此外,攝影評論張世倫在討論《鍊》的佈置時也認為,張乾琦不只是平面影像的再現,而是超越報導攝影的旁觀侷限,打開影像本身的物質存在。 (註)參照,張世倫〈毀壞的照片,燃燒的影像:試論張乾琦的《Side Chain》〉,《攝影之聲》,第14期(台北,2011)。
張乾琦在紀實的基礎上推進紀實攝影的語言,不管是影像的多媒體編輯、又或者是對肖像姿態的轉變,都讓我們不再只是停留在傳統紀實攝影個人表現的張力或美學,而是開啟我們跟他者之間的不可能距離,以及提醒傳統攝影想去再現現實的不可能性。如此一來更讓我們意識到,攝影不只是單純的「指引」(indexicality)現實,而是在現實基礎上透過某種虛構方式「創造新現實」。 這邊要小心,所謂新現實或虛構的創造不是個人的美學趣味,也不是天馬行空的奇幻(獨角獸或人在天上飛等等)。而是對於既有現實概念翻轉的「視差之見」(The parallax view)。
接著,我們將離開《微光闇影》當中對紀實的關注,更多元的關照其他創作者考慮攝影語言的其他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