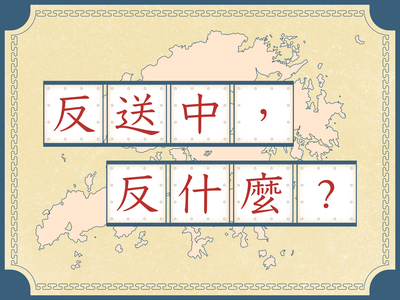很多香港人認為,這是97年香港回歸後最重要的選舉。政治新人、素人、社會運動者紛紛加入香港區議會議員選舉,而青年更是買機票返港投票,因為他們擔心,這「可能是最後的選舉」。層級很小的區選,卻史無前例地熱絡,讓社運人士和立法會議員在街頭遇襲也要選下去。究竟他們為何堅持?他們怎麼看這場選舉對港人的命運?
選前不到24小時了,香港氣氛顯得緊繃詭譎。昨天(22日)凌晨,在台港生組成的「香港邊城青年」在臉書粉絲頁發出呼籲:「我們一起回家,好嗎?」學生們說的是,返港投票。溫軟但悲傷的文字末尾是這麼說的:
那,讓我們一起回家吧。 一起回去守住可能是最後的選舉, 一起回去為香港盡自己的社會責任。 就算最後區議會選舉取消了, 我們還是可以在那一刻與香港手足,與我們的家人, 齊上齊落、並肩而行,一起攬炒也無所畏懼。
「可能是最後的選舉」、「就算最後區議會選舉取消了」,短短兩句話盡顯港人對於未來的疑慮與恐懼。
明天(24日)將登場的香港區議員是香港史上最受矚目的區選選戰,不只政治素人遍地開花,岑子杰、朱凱廸、梁國雄(長毛)、岑敖暉等社會運動者也投入選戰,近幾個月暴力事件頻傳、多人遭受資格審查,原本參選海怡西選區的黃之鋒也因「民主自決」的主張,遭取消參選資格。

10月16日晚上,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岑子杰遇襲,他躺臥血泊中的照片怵目驚心。遇襲後3週,我們與岑子杰約在香港立法會附近見面,他雙手拄著拐杖,一旁有朋友貼身保護。至少不用輪椅了,天色要暗了,我們央求他到添馬公園濱海處拍照,他小小聲咕噥:「那麼遠。」他其實還不太能走遠,但更讓他與友人疑慮的是,短短200公尺的距離,會不會又遭埋伏?
那是岑子杰兩個月內第二度遇襲了。二度遇襲前幾天,他才代表社會民主連線登記參選沙田區瀝源選區議員,取代2014年因佔中案遭判刑而無法參選的黃浩銘。登記後第6天,他獨自前往開會的路上遭埋伏,眼看著目的地就在眼前,他快跑趕開會,踏進大廈門前時,一旁車子裡竄出多位蒙面人,對他就是一陣猛打,重擊他的頭部與雙腳膝蓋,造成他膝蓋受傷,頭部留下3.5公分到5公分的多道傷口。
憶及當時,岑子杰顯得冷靜,「當時感覺不到痛,意識特別清楚。我可以感覺到,行凶的人是有控制能力的,我的骨頭沒有碎沒有裂,他不是用全力要我死,是要恐嚇我,要我受傷,要我走不動。」他在醫院整整躺了 3天,沒辦法下床走動。直到此刻,他仍需要單邊拐杖協助移動。但岑子杰還是繼續跑選戰,能自己街站就自己街站,親自對選民述說政綱。
岑子杰是民陣召集人,民陣是約50個組織、政黨、社團組成的聯盟,過去最常主辦每年的七一大遊行。反送中運動爆發後,多場大型遊行都由民陣發起,包括史上參與人數最多的二百萬人大遊行。6月12日,港警發出反送中運動的第一顆催淚彈,港府更將當天民眾運動定位為「暴動」。回應港府時,也是岑子杰數度堅定重申:「沒有暴動,只有暴政。」
8月29日,他與友人在餐廳午餐,突然遭襲擊,友人為保護他而受傷。接著就是10月16日遭埋伏重擊,問他當下痛苦嗎?他搖搖頭說還好,反而是急著想處理後續,躺臥血泊還請路人分工叫救護車、通知同事,接著幽自己一默:「早知道我那天就不抓頭髮了,受傷後9天沒洗頭啊,頭上都是血啊、汙垢、髮蠟、定型噴霧⋯⋯很可怕的!」
在一場沒有大台的運動裡,即使不是領袖,岑子杰還是太顯眼了。岑子杰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區議員助理,他熟悉社區工作,卻從來沒想過參選,直到反送中運動爆發,社民連徵召他參選,他才義無反顧投入。二度遭襲,沒想過退選?「沒有,我不怕的。」他很清楚這次的目標,「區議員雖然沒有多大實權,但區議員有責任說真話,把居民想法告訴政府。」
岑子杰說,今年5月底,有逾百校中學生連署反對《逃犯條例》修例,但香港區議會的18區主席們卻連署贊成修例。6月多時,曾有區議員提出要求撤回修例,但區議會想方設法讓會議流會,「很多建制派或獨立參選人會把社會跟社區政治分開,他們會說不要把政治帶到社區。」但生活怎麼可能跟政治無關?他忍不住想:「如果當時擋下來了,香港現在會是這般模樣嗎?」
反送中運動邁入第6個月,香港已遍體鱗傷。「每件事,每個人受的傷,都讓人難以忘記。最傷的是,我們曾經覺得香港是有制度的地方,但你看到現在,什麼制度形同虛設。」過去,岑子杰是運動組織者,但反送中運動至今,他覺得自己只是廣大群眾中的一個人,「我覺得這樣很好,我們都去做會的事情,大家都會走應該走的路。」他決定參選,投身社區,與遍地開花的政治素人點燃星星之火。

10分鐘、20分鐘、30分鐘過去⋯⋯路過的居民停下來,最後圍成一個小圈,認真地討論起社區裡的問題,好比近日催淚彈四射,該如何維持市民的健康。這是朱凱廸非常投入的時刻,後來他對我說,香港已經好幾個月無法好好討論議題了,「我們經常會做這樣的討論會,但最近幾個月,空間變小了,大家都很情緒化。這樣的討論,很不容易。今天真的很好。」
政治新人、素人在各選區遍地開花,像是運動戰場延伸到選戰。朱凱廸也觀察,「這次區選是香港97以來最重要的選舉,真正在政治上面有意義的選舉。」他也認為,這是香港人給中共最後的機會,也是市民給彼此的一個機會。「如果要維持一國兩制,你可以接受你失敗嗎?共產黨能接受自己失敗嗎?這一次是有可能翻轉的,中共可以接受嗎?如果可以接受,明年立法會選舉也可能變天。」

相較於5年前佔中後的區選,許多市民對抗爭運動的接受度遠遠不如反送中運動。「因為這次示威運動、催淚瓦斯發生在不同的社區,整個社區都搞動起來,社區開始有意識,我們要彼此保護,不能讓警察進來搞我們。」在選戰過程中,參選人與社區最需要磨合的部分不存在了,彼此共患難的意識非常高,全民對運動有極高的共同投入感。
如今的選舉氣氛非常微妙,朱凱廸是有些擔心的。「過去港人不太能感受到選舉在政治上的能量,但這次,大家都感覺到了。愈是感覺到了,就愈可能翻盤,愈是可能翻盤,共產黨就愈有可能翻桌。一旦中共翻桌了,以後還有選舉嗎?」
11月8日,年輕學生周梓樂過世當天晚上,朱凱廸到中環參與悼念行動,結束後搭船回到九龍島再轉搭巴士回到八鄉,下車慢慢走到家門口時,看見3個警察等在門口將他拘捕。同一時間,共有7名議員被捕,被指涉嫌在5月11日立法會的修例草案委員會上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19條。朱凱廸很清楚,違法只是藉口,更多的是警告。
過去幾個月,朱凱廸的手機頻頻遭到攻擊,與記者通Whatsapp也屢遭打斷,一通10分鐘的電話被中斷數十次,目的似乎要他噤聲。2016年他參選立法會議員時,也同樣收到恐嚇威脅,當時港警還出動保護他與妻女。今年區選,他又接到恐嚇,他只去警局備了案。還會想申請警察保護嗎?「不會了。現在不會想了。」
朱凱廸說起這幾個月最難受的事。幾乎每個禮拜,他都會去探視因反送中運動被拘捕年輕人,「他們也許完全不知道面對的是多長的牢獄?但我感覺他們的心態上都很有準備。」只是他忍不住會想,如果換成他呢?該怎麼面對?「有些人的犧牲,已經到我們沒辦法想像的程度。」更難忍受的是,可能有人還沒坐牢,卻被酷刑暴力對待,又或者已經送到中國。
他提起一個不到18歲的孩子,「他是勇武派,父母都不理他。被關之後,我們去看他,我應該是第一個去探視他的人,他當時的情緒緊繃到十多天沒有大號⋯⋯整個人一直在發抖。」像是回憶起當時,朱凱廸顯得憂鬱起來,他記得,那個孩子不斷對他說:「謝謝你來看我,真的謝謝你來看我。」朱凱廸很清楚,眼前的孩子即將面對的是什麼,「起碼得關4、5年吧,我想起來就非常痛苦,因為他可能不知道⋯⋯」
黑暗的日子裡仍有微光的時刻吧?朱凱廸是土地正義聯盟成員,過去長期關注城市規劃與公共空間議題,香港許多新地區都是資本控制的商場空間,難以公共化。但在這次運動裡,商場也成為政治空間,「這件事讓我很感動,每次看到大家在商場裡唱歌,我就非常感動。政府太小看人民了,人民其實可以比資本還要大。」是這樣小小的微光,讓朱凱廸看見人民大大的力量。
「以前常說香港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的地方,如今,我們已經知道,這個脆弱得無法想像,沒有防禦機制能自我保護。因為我們只是被給予自由,對方要收回就收回。這讓很多香港人重新去想,到底什麼是政治?什麼是民主?為什麼民主很重要?」朱凱廸是這樣解讀的,「以前香港人對民主半信半疑,不會確定民主是能保護自己的核心價值。但這次不同了,反送中運動為何能持久?其中一個關鍵是:大家不會再相信由其他人給予的自由了。」
回溯半年來的反送中運動,抗爭口號從「香港人!加油」開始,《禁蒙面法》頒佈後改為「香港人!反抗」,再到周梓樂過世後的「香港人!報仇」,轉變的口號也像是覺醒之路。或許如朱凱廸所觀察的,港人正開始思考:「民主是什麼?」岑子杰則給我們一個小小的總結:「我覺得,現在是『香港人!堅持』了。我們維持最長的是希望,不能失去的也是希望。」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