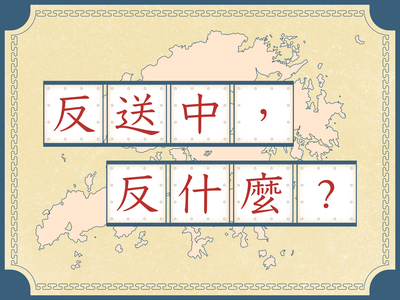香港反送中運動中,警察的濫權行為造成無形的恐懼,許多示威者在前線行動時被警察認出或記錄下了個人資料,他們因為擔心會被秋後算帳而被迫遠走他鄉,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展開生活。香港的網友不願意把這些義士說成是在「流亡」,都說他們只是去了「旅行」,盼望他們有歸來的一天。
「我已經有好多不同的名字了,你們就隨便稱呼我吧!」我們與旅行者Mike(化名)的第一次相遇就約在一個教會中略嫌壓迫的小房間。在幾次約訪逐漸建立信任後,Mike問我們要不要一起到他喜愛的餐廳用餐,對他來說,好好地享受美食是種奢侈的獎勵。
然而,那天到了約定時間卻不見Mike的蹤影,一問才知道安眠藥的藥效讓他睡過頭。我們稍候片刻,在他急忙趕到之後才開始用餐,過程中Mike不時看手機發語音,關心香港朋友在運動中的狀況,似乎不想放棄任何能幫得上香港的地方。
隔天,有人試圖在金鐘跳樓死諫,Mike聽到後立刻坐計程車去救人,卻也因自己的顯眼傷勢被警察注意到。
當時的Mike在前線運動已接近一個月,自己曾被警察抄下個人資料,加上看過不少同路人在被拘捕後被控暴動罪,Mike擔心自己會被警察秋後算帳,於是萌生赴台灣的念頭。沒想到這一走,就快半年。
離鄉是因揹著被整肅的恐懼。
12月9日為止,在港被捕的運動人數超過6,000人,是1967年香港左派發起「六七暴動」後,最多人被捕的社會運動。被捕者中,已有1,300多人被以暴動罪逮捕, 其中有519人被以暴動罪成功起訴。他們不但得面對多年的司法程序,若暴動罪成立,最高要面對10年的監禁。
像Mike一樣離港來台的旅行者並不在少數。
在反送中運動後,有人因對香港前途失去信心計劃移民到台灣、英國等國家;也有像Mike一樣怕被檢控入獄失去自由,對自己未來充滿恐懼的運動者。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規定,香港民眾在台申請居留可以依親、工作、投資或專業等形式申請,在台灣也有專門的移民顧問公司能協助港人落地生根。然而,對無根的「旅行者」來說,他們是這之中最不幸的一群。
無根的旅行者,在被警察盯上的幾天之內就得倉卒離開香港,行李都來不及整理妥當,更不可能有時間深入研究台灣的居留規定。
以Mike為例,沒有足夠經濟條件的他不符居留申請資格,緊急趕來台灣只能先申請6個月的短期停留(3個月觀光簽+3個月延期停留),如今6個月即將期滿,下個月人會在哪裡,他自己也說不準。
原本的學業、工作被迫中斷,在台灣也沒有辦法展開新生活,像Mike這樣的旅行者成為被居留條件遺落的人。
所幸,這群旅行者在絕望之際,還是有人向他們伸出了援手。一群台灣律師組成的「香港抗爭者支援工作台灣義務律師團」,以法律專業協助了遭遇法律困境的香港人。
律師與NGO合作,由NGO和民間團體先行了解港人的身心狀況、經濟條件,並確認當事人居留台灣的意願,再轉介律師團協助進行法律諮詢,並進一步與政府機關溝通。根據律師團成員陳雨凡估計,目前向他們求助的港人數目大約落在100以內。而這樣的「旅行者」,《紐約時報》在日前的報導粗估至少200位。
近期也傳出有港人以非法途徑來到台灣,「目前我們所有協助的當事人都是合法入境(指以觀光簽進入)的,」陳雨凡說明,「只要是有參與香港反送中,希望來台灣做一個比較長期的居留,我們都希望可以協助他。」
「最大多數都是良民證的問題,」陳雨凡補充,「包括就學、就業都要出示良民證,良民證又必須是香港那邊的警察機關開的,可是他們可能來的時候沒有,或是說他們要再回去拿是非常困難的。」
類似這樣的情況,目前共有約20位的律師在協助港人以個案的方式跟政府溝通,在欠缺法源基礎的機制下,義務律師的目標是讓個案順利居留。
面對不確定的居留狀態,年輕的流亡者惶惶不安地踏上台灣,一無所有之下,安穩的住宿成為奢望。
過程中,有民間團體、在台港澳人士,為他們安排暫時的棲身之所。也有熱心的旅館經營者跨縣市合作,每個月各自提供5張床位讓支持反送中的港人免費入住,對於短期來台的運動者是一大福音。
剛到台灣半個月後,Mike透過台灣友人認識願意幫忙的民間機構,找尋暫時安身的環境。曾想要租長期一點的房子住下,卻遇到房東不敢租房子給「流亡來台」的港人。 Mike自己就搬遷了好幾次,但所謂的搬家也不過是帶上從香港匆促塞進行李箱的衣服和來自親友的紀念品。
直到最近,Mike才終於和之前在反送中運動一起奮鬥、 同樣因躲避香港法庭檢控而來台的3位隊友住進家庭式套房,對這些旅行者而言,每天起床不用擔心晚上要睡哪,已是莫大的奢侈。
住宿的打理之外,三餐的安排也和半年前完全不同。「我每天只吃一餐,」Mike說,「因為在這邊預計也要長期生活,就更加節省一點。」曾經在香港餐廳擔任工讀生的Mike,平常就會在家裡開伙,主要負責家裡四個人的伙食 。香港人愛吃海鮮,Mike偶爾也會去市場買幾條魚回來料理,「台灣的海鮮比較便宜,但是這裡買的魚要處理很麻煩,一整條活的魚燙起來很麻煩。」
如果不像Mike擁有拿手的廚藝,許多旅行者也就像台灣人一樣,習慣在路邊的小吃攤填飽肚子。對生活津貼有限的他們來說,便宜又容易有飽足感的滷肉飯是最佳食物選擇,偶爾因為生日等特殊聚會,才可能吃得上一次烤肉吃到飽,抒發生活巨大壓力。

即使來到台灣,Mike也不曾退出這場戰役,日夜守著手機掌握最新消息,從前線與警方拚搏的勇武派,到退居幕後的後勤隊,香港的戰火燒了多久,Mike就戰了多久。
港警圍住理工大學的那幾天,Mike盯著直播焦急如焚、連夜無眠,熟悉現場地理位置的他,一心想的都是怎麼找路線把隊友救出來,深怕錯失了任何可以救援的時間。在連登、臉書、Telegram輪番查看,Mike不停刷新訊息,前線隊友出動的同時,他也在遙遠的台灣透過live location定位隊友的位置,分析地圖後協助安排動線,如果隊友被捕了,接到消息就馬上聯繫律師、找醫護人員。彷彿他身處平安的每一秒都想拿來為隊友爭取多一分的脫險機會。即使是香港情勢稍緩的日子裡,他依然在找能為家鄉做的事,被暴力籠罩的香港,徒剩下想守護的人。
理工大學被攻陷後,校方宣佈復課無期,許多學生也被警方留下了資料。基於跟Mike一樣的安全顧慮,又有一批香港人來到台灣,而來台已經半年的Mike,自然成為初來的港人尋求協助的對象。經隊友牽線,目前Mike已接觸了十幾位旅行者,這些人落地後的情況,一部分由他個人、教會協助,接住旅行者的還有其他民間團體。
「你在香港跑過來,在這邊能幫到的也不多,也只有這種,能幫多少就幫多少。不管是精神上的還是實際上的。」但Mike也坦言他其實有贖罪的心態,當朋友都遭警方逮捕,自己卻在台灣安好,好幾次衝動想飛回香港,冷靜下來又認清留在台灣才能幫上忙,回去也只是為被捕名單多加一員。就算心灰意冷,但現在每分支援的力量都至關重要。
看著反送中運動一路從和理非到現在年輕人不惜賭上未來,這其中的轉變,讓Mike認為香港真的覺醒了,一掃過去的保守性格,香港人改變了。「這個運動之中,我最喜歡的是可以見到香港人那種團結、人性的光輝,」Mike的眼神,帶著對自己家鄉的驕傲,「那種感覺從雨傘(指雨傘運動)以後,我是再一次感受到香港人那種無私的付出,其實這場運動之中我是滿感動的。」
但對香港城邦的付出,對自由和民主的渴望,是有代價的。日夜不停地關注運動,加上龐大的心理壓力,讓Mike的一天被迫延長,他經常在深夜裡折騰於失眠與惡夢之間。沒有身分證、健保卡的Mike,最初想服安眠藥還得委託台灣的朋友去藥局購買,「醫生說我應該是有抑鬱啊,那種創傷後遺症,所以精神方面,我有一陣子要吃安眠藥睡覺。」
睡眠過程不是發抖、醒來,就是做惡夢,港民受警察施暴、性暴力、跳樓等事件,夜裡埋伏到Mike的枕邊,他做惡夢不是夢到自己被打,而是那些受害者的經歷。長時間陷在香港情勢直播中,Mike愈發難以抽離,感覺有人還在受害的煎熬也讓自己難以接受,「我怎麼還這麼安全地在那邊逛來逛去,感覺平靜、和平不應該是我得到的東西。」
他被醫生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而這個狀況在香港示威者身上很普遍,許多旅行者也患有此症,但初來乍到的他們,光是來台後要安頓好生活就不大容易,心理壓力的排解自然被擺至最後,他們大多選擇自行承受。除非幸運一點的,遇上民間團體轉介醫生協助。
為了紓解心理壓力,Mike聽了醫生建議,多去外面走走,像是爬山、郊遊或是去台中的高美濕地;Mike也看了場電影,讓自己逃離現實世界的紛擾。他向我們展示包包裡的《冰雪奇緣2》飲料杯,杯蓋上頭有一隻活潑可愛的雪寶。在那刻,Mike彷彿普通的青春大男孩,而不是回不了家的示威旅行者。兩小時的電影是Mike一週當中少數可以不看手機的時候,「因為裡面可以強制性地不能拿起手機來看嘛。」然而短暫的抽離卻在電影播畢後,迅速接回了香港的現場,「天啊那個選舉亂象太誇張了!」Mike生活裡的每個縫隙,就是這樣被香港的即時資訊塞滿。
夜以繼日的警備狀況,Mike一刻也不得清閒。除了服用安眠藥,強制自己入睡外,上一次順利入眠,應是理工大學遭圍城那幾天,因太久沒睡而體力不支,昏迷在電腦桌前4、5個小時。令人心疼的是,被問到何時能真的放鬆,Mike卻說,是睡覺的時候。

離開家鄉近6個月,談起當初為他送機的家人與女友,Mike泛起了罕見的笑容。
他向我們透露,女友在前兩週曾驚喜現身台灣,「她來找我的時候我都不用吃藥,」即使另一半剛開始不能理解自己在這次運動中做的決定,在半年的遠距離溝通後,她終於逐漸接受運動的殘酷。兩個人都在台灣的週末,他們什麼也沒做,只是靜靜窩在家裡,陪在彼此身邊,共享亂世中難得的安定感。
出身單親家庭的Mike,在面對最親近的親友,還是得承受她們一時的不解。他甚至給母親留過遺書,謝謝她的陪伴,也請求她體諒他這個不孝的孩子,「我媽其實是意見相反,」即使經過無數次爭吵和流淚,他還是盼望母親能理解「為什麼這個社會要逼到年輕人這樣子做」。
相隔七百多公里,政治立場相左的母親終究難以割捨親情,打電話關心時,Mike總是回應自己過得很好,三餐都有吃飽。他也不忘提醒住在示威區的老人家,出門在外不要隨便摸、記得戴口罩。
電話掛掉後,他繼續獨自面對未明的前途。

回不了香港,也不確定能在台灣待多久,Mike的下一步在哪裡,沒有人知道。
「蔡英文政府看起來好像宣示了,說『我們會人道救援、個案協助』,可是在制度面上面,他們是消極的,」邱伊翎感嘆,「這些制度不夠清楚、不夠完備,最後就是讓第一線的民間團體等於是在處理一個燙手山芋。」
邱伊翎指出,《移民署組織法》第二條其實已明定其業務範圍包含難民之認定、庇護及安置管理,「但過去相關個案的人數實在太少了,所以他們(移民署)也沒有編列相關的人員去做這件事,甚至沒有這方面的訓練,所以不知道要怎麼處理這一類的事情。」放眼國際,日、韓、港、澳、紐、美等國家都有相關的審查制度以及相關權利保障的規定,邱伊翎呼籲政府應該借鏡外國的機制,並加強相關單位執法人員的培訓。
雖然《難民法》的問題經常因相關單位擔心中國因素介入難以認定難民資格,影響國家安全;但陳雨凡強調,在等不到《難民法》通過前,目前留台的港人,需要清楚居留的審查標準,「不清楚的情況下大家都亂做,或是各自揣測,我不覺得這個是好的方向。」
正值青春年紀的Mike,來台至今仍感到無所適從。「沒有找到留在這邊快樂生活的方式,就是普通地過日子而已,真的好像也是無所事事。」雖然喜歡台灣的自然環境,但Mike終究希望能完成自己的學業,找到生活的目的。
日子過一天算一天,隔著網路看同胞的抗爭,Mike也不曉得自己與香港的未來會變得如何,人生也因此被迫快速成長,然而,這趟沒有歸期的旅行還是得繼續走下去。
「我們也是走在一片黑暗之中,你不走下去,跑遠一點的話,你怎麼能看到,可能前面會有一點光。」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